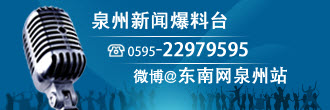引起轰动的后渚宋代古沉船
后渚说 宋代古沉船出土自后渚港,元史记载从后渚出兵征爪哇,郑和船队曾在后渚停泊
南关说 旅游名家关于刺桐港的场景描绘在城南,城区扩建一直向南,市舶司设置在城南
它,曾被世界航海家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千百年前“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
它,在世界航海史上曾独占鳌头400年,正待时日重整雄风。
它,就是古刺桐港。遗憾的是,在历经千年风雨之后,扬名海内外的古刺桐港中心港区“具体位置在哪里”,至今还有很大的争议。
日前,泉州七中退休教师陈清泉“临近手术室前叫女儿送信到早报,披露耗时10多年考证出有9个古渡口埋在江滨路下”一事(详见早报3月20日A16—A17版),不但感动了许多同样热爱泉州文化的市民,也引起了泉州文史界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陈清泉认为,这9个渡口从旧顺济桥北岸自西向东延伸、均匀布列在长达700米的深水岸畔,正是“古刺桐港所在地”。
一石激起千层浪。连日来,针对陈清泉“古刺桐港在城南”的考证结果,泉州文史界反响热烈。尽管他们普遍认为“古刺桐港是一个港口群,应该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密布的诸多支港”,但对于“在这个范围广袤的港口群中,中心港区的位置在哪里”,双方各持己见。
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庄为玑就提出刺桐港由“三湾十二支港”构成,且后渚港为宋元时代刺桐港的中心。此外,庄为玑教授等人在后渚港发现宋代古沉船,并从《元史》中发现“自后渚港出兵征爪哇”的记载,至今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后渚港即刺桐港中心港口”的主要证据。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泉州海交馆原馆长王连茂则认为,古刺桐港的中心由城南直至法石一带的沿江码头所组成,而“后渚港即刺桐港中心港口”的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也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商船进入泉州湾后,为何不沿着晋江的出海口溯江而上,直接停靠于城南的码头,而要舍近求远,在10公里之外的后渚港卸货?如此二度运输所造成的耗时费工、商业成本增加,是不言而喻的。
□早报记者 赵鹏云 颜雅婷 潘登 文/图

站在晋江沿岸的美山古渡口上,眺望历史。
后渚出土宋代古沉船
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古沉船轰动世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出土木质海船,可载重200多吨。古沉船的发现者之一,正是提出“后渚港即刺桐港中心港口”的厦大教授庄为玑。此后,不少学者便沿用庄为玑的说法,认定宋代古船的出土是“刺桐港中心港区即是后渚港”的主要证据之一。
林少川:“后渚说”的提倡者在后渚发现古沉船
据林少川介绍,庄为玑教授“倾一生之力”研究刺桐港,著有《古刺桐港》一书,并于1973年发现了宋代古沉船。但据记者了解,在庄为玑的著述中,并未直接提出古船出土与“后渚港是否为刺桐港中心港区”之间的联系。
当年,庄为玑到后渚调查,在一名运输工人的指引下,首先发现一个以木为基码的古码头,在附近捡到宋代陶瓷片三块。庄为玑认为,“元代兵船这样多,一定不止一个码头”。随后,庄为玑等人在后渚港海滩发现了古沉船。
在庄为玑看来,后渚港在蟳埔之前,为晋江下游主要港口,地位重要,海防建设也较蟳埔、法石为多。在后渚山腰中,他们曾发现一处明朝抗倭遗址;在附近看头乡的金山上,发现了金山寨。后渚南面有元五石塔,残迹尚在滩上。塔身刻有僧、法、宝等字,俗称镇风塔或风水塔。沿途有天妃庙七座。天妃为海神,宋以后沿海祀者甚多,说明这一带是海上活动繁盛的区域。
庄为玑在著作中说,1974年,他们再次到后渚调查时,发现后渚通泉州有三条古道。在山上古路边,发现有“修路碑”一方,又有洋墓、洋店,还有古墓碑及瓷片堆积层,可知是通泉州城的古大路。
另据林少川称,他从史料中了解到,作为元朝时期泉州的主要港口,后渚港承担着巨大吞吐量的货运。从后渚到市区的水路交通,沿洛阳江口南下至晋江出海口,折西溯晋江而上,经蟳埔、法石、溜石,到厂口街,抵顺济桥码头,沿破腹沟到三堡,入八卦沟,过水门关,到舶司库装卸货物,从后渚到市区的涂门、仁风门、车桥,陆路有4条。
王连茂:古船船员遇上战乱,将船抛在偏僻后渚
从宋船在后渚港沉没的原因方面分析,王连茂认为,这一点恰好能证明刺桐港中心在城南,而不是在后渚。
王连茂说,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都参与过对这艘古沉船年代的考证。由于沉船出土的铜钱中,年代最晚的是咸淳七年(1271年),这也是南宋最后铸造的一种钱,据此判断海船的年代是在此之后。有专家考证了船舱中果品的残物,按该果品成熟上市的时间顺序,依次有椰子、桃、杨梅、银杏、橄榄和荔枝,从而得出海船于6—7月间沉没的结论。有的专家对船舱出土的贝类和古船中的钻孔动物,如船蛆等进行研究,以其产卵、生长繁殖的时间及海水的盐度与温度,也得出海船在7—9月沉没的结论。
1276年底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落入元兵之手。第二年7月,退至广东新会的南宋军队乘元兵出征西南,蒲寿庚势单力薄,立即反攻泉州,围城三个月,因元军救兵到,乃解围而去。鉴于此,一些地方史专家认为,海船就是在这个时候乘东南季风回航的,遇上双方剧烈交战,不敢进到城南码头,只能抛在后渚,人员逃散,船上货物或许已起卸部分,或许遭遇抢劫。这正是台风袭击泉州的季节,久而久之,船便慢慢沉没了。

已经坍塌的旧顺济桥建于宋代,见证了城南的繁华。
从后渚出兵征爪哇
《元史》爪哇传云:“至元廿九年征爪哇……十二月自后渚起行”。《新元史》世祖本纪亦云:“至元廿九年,大军会泉州,自后渚起行”。这些文献记载,是一些学者认为“刺桐港中心港区即是后渚港”的另一个主要证据。
庄为玑:后渚为中心港口 元时出兵征爪哇
庄为玑中认为,刺桐港是一个大港群,由几个海湾的支港合并而成,总称之为“三湾十二支港”,即泉州湾的洛阳、后渚、法石、蚶江四支港;深沪港的祥芝、永宁、深沪、福全四支港;围头港的金井、围头、石井、安海四支港。后渚港在泉州湾的西岸、洛阳港的西南,为宋元时代刺桐港的中心。在《古刺桐港》一书中,庄为玑正是引用《元史》和《新元史》的记载,证实了上述这一观点。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庄为玑曾多次到后渚调查,发现港边有五个风水塔,塔上有铭文。铭文中称:“至元癸未仲夏(1283年)……后山杨应祥造。”由此可知,在元征爪哇之前九年,五小塔是后山乡船主杨氏造船祀神的风水塔。
1972年,庄为玑到后山乡调查时,借阅过《后山陈氏族谱》,看到谱内有许多造船记录,“使我确信元代后山乡确有造船的历史传统,杨氏也许和当时蒲寿庚造战船有所联系”。
王连茂:从后渚出兵最理想 不扰城南海上贸易
对于元军舰队在出征日本和爪哇之前集结于后渚港一事,王连茂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渚港为集结地是最理想不过的,这里枕山面海,水面宽阔,又较为隐蔽,开往台湾海峡也方便得多。倘若排布在晋江下游,航道受阻,人民惊恐不安,海上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岂不是损失巨大,“须知泉州是蒙元朝廷第一个宣布恢复市舶司、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王连茂认为,军事港口与商业港口是不一样的,军舰集中于城市南边的商业港口不太可能,另泉州湾比较宽敞,支港多,船舶可随处停靠,但商品货物的起卸货,则一定要在靠近泉州城的城南一带码头。

位于水门巷的市舶司遗址,昔日的古渡码头已湮没在水沟中。
城南江面是否够宽
如今,站在旧顺济桥头举目望去,江面仅有两三百米,很难看到宋元时外国旅游家记载的场景。因此,“后渚说”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城南的江面太窄,无法驶入和停泊大型海船,不可能是中心港区。但“城南说”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宋元时晋江下游江面远远比现在广阔,只是数百年来泥沙淤积,才让江面宽度缩小。
陈鹏:城南江面狭窄 后渚才能停泊大船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鹏认为,刺桐港在历史上有“内、外港”之分。南关港是内港,由于江面比较狭窄,只有小船才能出入,大的船舶无法驶入,后渚港发现的宋代古沉船,长34米、宽11米、载重200吨左右,“这么大的船,是进不了南关港的”。伊本·白图泰所描述的刺桐港“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南关港不具备这么宽阔的江面。所以,在庄为玑教授提出的“三湾十二支港”中,南关港没有列入其中。
陈鹏说,后渚港是外港,背山面海,水道较深,是个很好的避风港,便于大型海船的停泊和起航。在宋元时代,后渚港作为刺桐港的中心港口,比较大的外事、军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除了元兵出征爪哇外,1291年,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也是从后渚港出发的。
王连茂:到了清末民初 城南还停许多大船
难道当年的晋江下游果真淤浅到不能通大船吗?王连茂认为,即使到了清末民初,依然能够看到在新桥头(顺济桥北)所聚集的郊商大商行,仅宁波郊一途,就有40多艘乌艚型大帆船,从北方诸港、台湾和厦门运来的各种土特产、米、水果等,都在法石与新桥溪码头抛锚,部分货物起卸入仓库,部分留在船舱,再用小船运往各小港。
王连茂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石大商家伍嵩如父子租用的轮船,也直接运货到此地。这些船只的载重量并不比宋元商船小,而且更大。到了上世纪60年代时,几位健在的郊商曾这样忆述城南商业区的繁闹景象:“泉州市场真是万商云集,轮船一起货,富美、新桥头、南门兜等处,熙来攘往,热闹异常。”这充分证明了,历史上泉州港的中心港区,即是由城南直至法石一带的沿江码头所组成的。20世纪的大商船犹能进到这里,六七百年前的宋元时代,江面更宽,河道更深,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更何况宋元之际,蒲寿庚建“海云楼”“以望海舶”,他的庞大船队就停泊在法石一带的江面。
泉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泉州海交馆馆长丁毓玲也表示,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每年都对晋江河道进行清淤。
所以说,港口与城市紧密相连,从而形成港市一体化的商业城市格局,乃是当年泉州港最突出的特色。
其他声音之后渚说
郑和船队停泊后渚
尚有“接官亭”遗址
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玉昆认为,后渚港是宋元时期泉州的主要港口,承担着巨大吞吐量的货运。在他看来,刺桐港包含内港和外港,而南关港是一个内港,“宋元时,大的商贸船停靠后渚港后,再换小船或者通过陆路进泉州城”。
李玉昆从三个方面佐证后渚港才是刺桐港的中心港区:宋代古船在后渚港的出土;《元史》曾载元兵集结于后渚港,并从此出兵爪哇和日本;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曾停泊于后渚港,“从地理环境而言,后渚港较适宜大船停泊”。李玉昆表示,明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中,船队曾在泉州后渚港一带候风,并到百崎拜访郭氏族长郭仲远,“那时候,郑和的船队就是停靠于后渚”。郭仲远带领子嗣到百崎乡的白崎渡口迎接郑和,渡口的“桥尾亭”也因此得名“接官亭”,至今尚存于世。
其他声音之南关说
城南港城紧密相连
沿江设有修造船厂
泉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泉州海交馆馆长丁毓玲认为,作为地理历史概念的泉州港,应该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的各个支港,而中心港区则应在位于泉州城南直至法石一带的沿江码头所组成的港区。这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佐证,包括历史上城南一带一直是泉州的商贸中心,港口与城市紧密相连,且沿江岸设有修船、造船厂等。据悉,元末时,泉州曾编纂《清源志》,详细记载了宋元盛景。遗憾的是,该府志很快就失传了。
丁毓玲认为,过去学术界因后渚沉船将后渚港作为刺桐港的中心港区一说比较片面。“学术需要更加缜密的思考。”
其他视角
史籍表述、古城建设、报关路线
一份刺桐港考证报告的视角
2002年10月,由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等联合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学术讨论会”上,现任泉州电视台闽南语频道总监的戴泉明曾发表《刺桐港考证及其申报“世遗”的文化意义》学术报告。戴泉明称,从史学家的文章看,刺桐港一般作为历史概念,用于泛指泉州湾诸港口。专门考证刺桐港确切地理位置的文章,很难找见。
史籍表述:史籍中的刺桐港是一个具体的港口
戴泉明说,在庄为玑的“三湾十二支港”一说中,并没有南关港。而且如此广袤的范围,与1292年马可·波罗所看到的,即“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穿梭而出名”的历史场景很难相对应;与1347年伊本·白图泰所描述的“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深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的地理环境也难相符。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看到的刺桐港分明只是一个具体的港口,而不是12个分散的港口。
此外,元人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中所记载“一城要地,莫胜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的港口方位,也远非后渚港之所在。
古城建设:城区扩建一直向南临近港口商业繁荣
戴泉明说,自唐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武荣州治由丰州迁往东南的泉州平原之后,从历次大的城市扩建来看,一直是向濒江的南面发展。这是因为自泉州海外交通开始以来,外舶来泉皆停泊于城南晋江沿岸,因此城南晋江沿岸一带为外商之居留区,“商业繁盛甲于全州”。
戴泉明说,由于宋廷规定“化外人,法不当城居”,故镇南门一带一直是海外番商居住的社区。清真寺、印度教寺、顺济宫以及当代发现的大量伊斯兰教墓盖石、其他宗教遗物大都是在宋代镇南门以外。
从泉州古城的建设史看,如果刺桐港是后渚的话,城市扩建应向东面发展,但史实并非如此。另外,后渚至城区路途有20多公里之遥,舶货乘潮溯江而上即可在城南一带上岸卸货,又何苦将货物从后渚上岸再改为车马运输入城增加费用呢?况且,从后渚运货进城要翻过三四道山梁,运输上会遇到很多麻烦。
报关便捷:市舶司旧址在城南商人可就近办手续
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朝廷批准泉州设置市舶司。当时,商人到海外贸易,需向市舶司呈报出国船只、人员、货物,经验实后,市舶司签发公凭(即“出海贸易许可证”)。回国后,从原发舶港缴上公凭,并就地上缴实物税。
戴泉明认为,泉州市舶司所在地及其“报关”路线,为确认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明。据清《晋江县志》记载:“宋市舶司,在水仙门内,即旧市舶司址。”《泉州府志》称市舶司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毫无疑问,宋市舶司就在今水门附近。由此可见,宋代泉州商人在出海去国外之前,应当是将大船停泊于南关港,而后乘小舟沿巽水(今“破腹沟”)而上,入水门关到市舶司办理出入关手续。
戴泉明说,由于河道淤塞,后来南关港逐渐向顺济桥南一带延伸。南宋末,南关港与法石港已连成沿岸港口。1272年,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来泉州时,看到的场景是“这儿有成批的商人沿江而下……在江堤边有许多装着铁门的大仓库,大印度及其他地方的商人以此来确保他们货物的安全”。另外,从目前存世的一些碑记、史籍中的记载,均可证明直到清代,南关港始终是泉州重要的集散港口,而后渚港无此类史迹或记载。
延伸
泉州海交馆馆长丁毓玲:感谢早报报道 有助厘清历史事实
“早报关注刺桐港的这组报道,有助于厘清历史事实,非常好!”泉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泉州海交馆馆长丁毓玲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泉州学术界对于刺桐港的研究还不够,曾作为历史上的“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它是一个港口群,但关于这个港口群中心港区的具体位置,却缺乏真正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丁毓玲认为,早报的报道提出了许多更加细致的问题,而这正是学术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她认为,早报的报道有助于将刺桐港的研究引向深入、细致的方向,更有助于厘清历史事实、普及历史知识,让泉州人更明白、清楚地知道历史上真正的刺桐港中心港区位于何处。
|